
✪ 杨平 / 文化纵横杂志社长
《文化纵横》微信:whzh_21bcr
伏尔塔瓦河的美丽旋律,对我这一代人相当熟悉亲切,它缘于德沃夏克的《新世界交响乐》,英文《From Now World》,又名《自新大陆交响乐》。
上世纪八十年代,改革开放伊始,一个新的时代启幕,笔者尚在黄海之滨的胶东半岛当兵,闲暇之余偶自收音机中听到《新世界交响乐》,一下子被它深邃隽永的旋律打动,其第二乐章中浓重的思乡之情深深地攫住了我的思绪,关于故乡,关于北京,关于亲人和朋友,关于未来的期待……
30年后,沧海桑田,故乡北京已有惊人之变,黄海之滨的青年士兵业已壮年,并阅尽人间沧桑。2012年的冬季,偶然的机缘重新听到《新世界交响乐》。刹那间的感觉犹如触电,关于音乐,关于新世界,关于故乡,关于我这一代人的人生,一瞬间如排山倒海,呼啸而来……
一
那是一个冬季的北京夜晚,太太的好友吕绍嘉从台北来京演出,他是台湾爱乐乐团的艺术总监,巡历欧美并获世界声誉的音乐翘楚。应他的邀约,我们来到国家大剧院的音乐厅,参加台湾爱乐乐团的演出季。曲目中压轴的是德沃夏克的《新世界交响乐》。这乐曲已经多年未听,但旋律的熟悉是自不待言的,我们静静地进入演奏者为听众安排的音乐世界中。
第一乐章,那是喧嚣的新大陆,北美新世界的壮阔、雄伟、想象力,工业革命卷起的浮尘和欲望,还有各种人间所可能创造的奇迹,在德沃夏克的旋律中震荡。乐曲间的副部主题是种犹豫怯懦的调子,面对滔滔的人间洪流,不知是勇敢的投入,还是冷冷的旁观。作者的主观是激动、热烈,夹着彷徨、犹豫。
第二乐章,回到欧洲旧大陆的故乡,那是东欧平原的斑斓多彩,那是伏尔塔瓦河的波浪起伏,那是故乡平川上寂静古老的小屋,那是几个世纪如一日的安详宁静。故乡呵故乡,它是面对北美新世界壮丽辉煌情境的映像,它是现代化奔腾向前波涛汹涌激流澎湃大势之下的避难所。在德沃夏克的旋律中,旧大陆被美化了。因为新大陆的冲击实在令人无法阻挡,代表着工业革命,代表着现代化,代表着未来的新世界,怎能不让人去寻找旧世界的心灵栖息地。
第三乐章,两个世界的主题激烈冲撞,交替呈现,相互激荡,新世界的壮阔激情随时伴随着旧世界的委婉温情,对于未来的无限憧憬时刻被复古怀旧的故乡之思纠缠,过去、现在、未来……音乐最后终止于犹疑之中,仿佛交由听众自己选择新旧世界的出路。
那一晚交响乐的效果令人惊诧,当第二乐章展开时,我便开始泪流不止,并不断用手拂拭怎么都止不住的泪水。30多年了,当我再次听到这首交响曲时,我的故乡已经不是当年的故乡,整个北京,整个中国,经历了狂飙激荡的工业化洗礼,犹如德沃夏克曲中的新大陆,世界变了,人心变了,我的故乡丢失了。面对过往,怅然若失,面对未来,歧路彷徨。

二
2012年,我生活中发生了两件事。一是父亲去世,一是我开车撞了人。
那年4月,92岁的父亲离开了我们。他的逝世是相对安详的,在经历了三个月的治疗接近出院时,突发心肌梗塞,几天之后便离开了人世。50多岁的我,早已自觉顶天立地,但也突然觉得天塌了。丧父之痛,对于男人而言,是摧毁式的。
父亲是安徽无为的农民,年轻时当兵打日本,随共产党征战天下,历经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、抗美援朝,建国后在国防科工委后勤部门工作,并经历了建国后的各种政治运动和文化大革命。他是典型的农民,温和、朴实,善良中不乏农民式的狡猾,在军队中他以服从命令作为安身立命之本,并自觉认同毛泽东一代开创的社会主义基本价值。1980年代中期他便离职休养了,因此他对世界的基本判断和依据多来自这个时代之前。改革开放的30年他算槛外之人,自身命运没太受到影响,如果说有什么深刻变故的话,他知道这个时代只认钱了,没有钱什么事都办不成。对此他虽多有牢骚,偶而骂骂娘,但如同多数中国传统农民一样,他知道顺应大势。
但在家庭伦理上他却是典型的老顽固,必须儿孙绕膝、父慈子孝。每逢周末,不管你多忙,他都必然电话来催,让回家吃饭,稍有差池,便破口大骂。这种老父亲电话催逼回家的压力,至今我依然还有。年轻时会埋怨老人家不谙世事,不知当代人生存压力有多大,总是以他那个时代的伦理要求当代人,但慢慢也就习惯了,知道他无法改变,顺着他、哄哄他也就算了。
父亲走了以后,我突然觉得家没了,我与家庭、故乡、传统的联结点中断了。2013年4月,父亲周年纪念日,我与全家来八宝山革命公墓为父亲扫墓,骤然间发现,父亲墓前墓后、墓左墓右全是军人,墓碑刻辞也大致相同,比如“戎马一生,鞠躬尽瘁”,比如“革命一生,战斗一生”。我转头对女儿、外甥和家庭的后辈说道:“你们要记住,你们是革命的后代”。
我的故乡在北京,它是父母壮年后生活的地方,并在此哺育养大了我。30年前的故乡是红色的,它由社会主义的红色价值和古老传统中的红墙构成,30年后的北京红墙已日益少见了,社会主义的红色价值也色彩斑驳,整个北京城被工业化现代化彻底洗礼,城市变了,人变了,往日的北京风貌只能在被修饰过的古迹中寻找,那仿佛旧大陆的美丽温情的故乡北京已经丢失,它随着我父亲母亲的故去成为记忆中的历史。而澎湃的新北京正好似德沃夏克曲中的新大陆一样汹涌而来,我被这雄伟、华丽、喧嚣、冷漠的新北京裹挟前行,人生几乎被完全重新塑造。思念及此,当《新世界交响曲》重新响起时,怎能不泪如雨下。
三
父亲去世后的两个月,我开车撞了人。那是一个来自吉林白城的农民工,酒后微醉横穿五环主路,在内侧车道被我的车撞个正着。眼瞧着已经飞起来又重新撞向我车前挡风玻璃的人,我心想,完了,要死人了。
也算奇迹,停车后七手八脚地处理完毕,发现人居然活着,而且一瘸一拐地独自走向路边打起电话。我电话叫来120救护车和警察,并好言劝慰伤者和前来帮忙的伤者家属。我告诉伤者的女儿,别担心,我不会不负责的,法律上该怎么处理另说,但一定要全力救人,我会出钱并管到底。令我没想到的是伤者家属十分蛮横,纠集一批同乡上来就要动手打人,幸亏警察及时赶到,隔开了双方。这以后就是漫长又麻烦的救治和责任追究及赔偿过程,这一过程让我明白了现代法治的复杂和纠结。
按警察的说法,在中国,撞了不能白撞,机动车和行人发生碰撞首先是机动车的责任,然后视行人的责任再酌情减轻机动车的责任。虽然这位农民工是横穿五环主路,责任不小,但我必须承担责任。经过警察一番调解和恐吓,我们双方各自承担了50%的责任。这以后就是漫长的赔偿纠缠,对方家人提出了大量不胜其烦的赔偿要求,而事实上人伤的并不重,当我看到事情的处理完全不能依人的善意和主观能动性解决时,只好跟对方走上法庭。法庭判决的结果是保险公司承担了主要赔偿费用,我则负担了赔偿的30%。
事情过后,我开始思考这其中的含意。因为父亲刚刚过世,我又差点出了人命,它的刺激不言而喻。
作为已经现代化的城里人,我在高速路上驾车,没有任何过失,而那位农民工则是个前现代的农民,完全不具备现代交通与法治的概念,他横穿五环主路,以为与过家乡门前的马路差不多。虽然从法律上他要对其非现代的行为负责,但作为弱者,中国的法律又不能简单规定撞了白撞。于是,矛盾和麻烦就开始出现在我这个现代人和他这个前现代人之间。我开始以人道和善意来解决问题,这意味着我又回到前现代的价值体系和规则体系中,但结果证明并不管用。因为对方发现,只有犯刁才能维护自己的利益,而犯刁或狮子大开口一旦不管用,法律是他保护自己的最好办法,谁让中国还是社会主义国家,居然规定撞了不能白撞的法律呢。回过头来检视我的行为,就发现非理性的矛盾之处了。如果从一开始我就将现代人的逻辑贯彻始终,从法律上坚持自己的利益,不承担那50%的责任,至少将其推卸至30%或10%,我的责任就小多了。由此我想到,为什么那么多的交通事故纠纷牵扯不清,为什么那么多的司机撞了人之后逃逸,为什么广东佛山小悦悦被撞事件中司机和路人的行为如此冷漠,原来,按照现代法治社会的内在逻辑,他们的行为选择其实是理性的,符合法治精神的,而其选择救人或按人道主义原则处理,则是非理性的,违背现代法治精神的。
一个撞人交通事故,使我看到了自己身上的非现代人一面,我不能按照理性计算和利益最大化原则来处理矛盾纠纷,内心里依然残存着古老的中国人的处事法则和社会主义的道德遗产,我不为此付出代价才怪。而反观被撞的那位农民工,他由纯朴的农民要适应现代都市社会,最可能的选择就是变为刁民。由此推衍,那千百万大批的农民,他们要从传统人变成现代人,从古老的互利互惠的伦理中变成一事当前讲求自己权利的人,其间该造出多少既非传统又非现代的刁民呵。
四
在2012年的深冬,辉煌的国家大剧院里德沃夏克的《新世界交响乐》,深情的伏尔塔瓦河旋律,让一个已届壮年的现代都市人泪流满面。
30年后的中国,30年后的北京,故乡已经不在,人性也已大变。新大陆扑面而来,新大陆以其强大的逻辑塑造着我们这些从旧大陆迁徙而来的乡民,它以其物质财富的强劲增长,以其货币价值的冷漠无情,以其现代法治的契约精神,以其强烈的竞争法则,促使我们迅速地卷入其中。我们匍伏在地,焦虑不安,四顾茫然,不知何处是岸。
当此之时,我又怎能不痛哭失声,伤彻肺腑。
2013年10月
(本文原载《艺术手册》。图片来自网络。版权所有,欢迎个人分享,媒体转载请回复微信whzh_21bcr获得许可)
 关于我们
关于我们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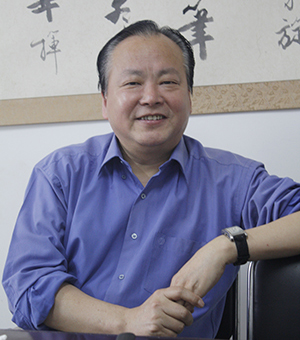 修远基金会理事长 《文化纵横》杂志社社长
修远基金会理事长 《文化纵横》杂志社社长


